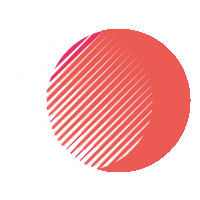指导性案例第266号“黄某欢诉某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背景下,人民法院对“先享后付”信用服务模式作出正面评价的标志性案例。该案并未简单停留在“是否取得同意”的表层问题,而是围绕个人信息处理的合同必需性、告知充分性及最小影响原则,对信用服务商的行为进行了体系化审查,为同类纠纷提供了清晰裁判逻辑。
一、案件事实与技术应用场景
黄某欢在使用手机应用开通电子公交乘车码时,选择了“先享后付”功能。该功能的运行机制在于,当用户乘车时若无法即时支付费用,由第三方平台先行垫付车费,后续再向用户追偿。为实现该功能,相关平台需在服务前对用户信用状况进行评估。
在开通过程中,页面以显著方式提示用户需同意相关服务协议和授权协议,协议中载明将获取用户的身份信息、履约信息及与信用评估相关的必要信息。黄某欢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其被开通了信用账户,随后主张相关信用服务商未经其允许收集、处理其个人信息,构成侵权。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本案并非发生在“被动开通”或“暗箱收集”情形,而是发生在用户主动选择特定功能的背景之下。
二、争议焦点的法律结构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在“先享后付”这一特定应用场景中,信用服务商为履行服务合同而收集、处理用户信用相关个人信息,是否构成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
该问题实质上指向三个关键判断维度:
一是相关信息处理是否属于订立、履行合同所必需;
二是信息处理者是否依法履行了充分的告知义务;
三是信息收集范围是否符合最小必要原则。
三、“合同必需性”作为合法处理的正当基础
人民法院首先从合同履行角度对信息处理行为进行评价。法院明确指出,“先享后付”服务的本质在于第三方先行垫资,信用服务商因此面临真实、可量化的资金风险。在此情形下,事前评估用户的信用和履约能力,是决定是否提供该服务的前提条件。
由此产生的信用信息收集行为,属于为订立、履行以用户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同所必需,具有正当业务目的和现实合理性。
法院在此强调,个人信息保护法并非否定一切商业信用评估行为,而是要求其具有清晰、正当的合同基础。
四、告知义务的实质履行而非形式存在
在告知义务方面,法院并未采取“是否弹窗提示”的形式化审查,而是关注用户是否具备真实的知情可能性。裁判认定,相关协议在开通页面以明显区别于普通文本的方式展示,用户可点击查阅完整内容,且对个人信息处理条款采用加粗、标色等方式进行提示,足以引起一般用户注意。
同时,协议明确告知用户其有权选择其他支付方式乘车,亦可在事后关闭授权、注销信用账户,用户并非被强制接受信用服务。
告知义务的核心不在于“有没有协议”,而在于是否给予用户真实、可理解的选择空间。
五、最小必要原则在信用服务中的具体适用
针对个人信息保护中的“最小必要原则”,法院进一步作出细化阐释。裁判指出,信用服务商并未向第三方披露完整的个人信息明细,而是仅向合作方提供是否符合服务准入条件的结论性判断。
这种处理方式,使个人信息的使用范围被严格限定在实现“先享后付”功能所必需的最小程度,未对用户权益造成不必要扩张性影响,符合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要求。
最小必要原则并不要求“零收集”,而是反对“过度收集”。
六、对“捆绑”“强迫”指控的否定
针对用户主张的“捆绑开通”“强迫授权”问题,法院结合具体应用场景予以否定。裁判指出,用户仍可选择现金投币、实体公交卡等多种替代方式完成乘车,电子乘车码及其“先享后付”功能并非唯一选择。
同时,服务协议中明确载明退出路径,用户亦可随时关闭授权。由此可见,相关信用服务并未剥夺用户的自主选择权。
是否构成强迫,应以是否存在现实替代方案为重要判断标准。
七、裁判规则的体系化提炼
通过本案,可以清晰提炼出一项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裁判规则:在“先享后付”等信用服务场景中,信用服务商为订立、履行合同,以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用户信用相关个人信息,并依法履行告知义务的,不构成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
该规则为信用服务创新提供了明确的合规边界。
八、对个人信息保护与律师实务的启示
从个人信息保护实务角度看,本案提示判断侵权与否,不能脱离具体业务场景和合同结构。并非所有未经单独同意的信息处理行为均当然违法,关键在于是否满足法定处理事由及比例原则。
从律师代理角度看,在处理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时,应重点审查服务是否具备合同必需性、告知是否充分、信息使用是否受限,而不宜仅围绕“是否点过同意”展开单一论证。
个人信息保护的核心,是平衡而非否定。
结语
指导性案例第266号通过对“先享后付”信用服务模式的系统审查,明确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新型商业模式中的适用尺度。该案既为信用服务的合规运行提供了司法背书,也为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确立了可操作、可预期的判断框架,对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个人信息争议具有长远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