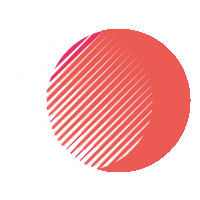余某鸿、某社区居民委员会申请指定监护人案,是近年来成年监护制度适用中极具代表性的入库案例。该案并未机械适用“近亲属优先”的形式规则,而是通过对被监护人真实意愿、近亲属监护能力以及潜在风险的实质审查,明确了在特殊情形下,由基层自治组织担任监护人的正当性边界,对同类案件具有高度示范意义。
一、案件背景与监护关系的现实困境
余某甫与许某丽系夫妻,二人未生育子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依法收养余某鸿。进入老年后,夫妻二人先后因精神、认知障碍被人民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生活照料与财产管理问题逐渐凸显。
在监护安排上,余某鸿以“子女身份”为由,申请由其与某社区居民委员会共同担任余某甫的监护人;而某社区居民委员会则在尊重老人意愿的前提下,单独申请担任监护人。余某甫本人多次明确表示,不愿意由余某鸿担任其监护人,而希望由居委会担任。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本案并非监护资格当然缺位,而是存在“近亲属具名但不被信任”的现实冲突。
二、争议焦点的法律结构
本案的核心争议集中于一个关键问题:在被监护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成年人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在近亲属与基层组织之间作出监护人指定选择。
该问题实质上涉及三项价值的平衡:
一是法定监护顺序;
二是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三是监护人履职能力及风险防范。
三、法定顺序并非绝对优先规则
民法典明确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其监护人原则上应当由配偶、父母、子女等近亲属依序担任。但人民法院在裁判中强调,该顺序规则并非僵化适用,而应服从于“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
当具有法定顺位资格的近亲属,存在不利于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形时,人民法院有权依法突破顺序限制,选择更有利于被监护人权益保障的监护方案。
近亲属身份,是监护资格的起点,而非当然结论。
四、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独立价值
本案中,余某甫虽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司法鉴定意见明确,其认知能力并未完全丧失,仍可表达与自身重大利益相关的真实意愿。
人民法院据此认定,余某甫关于“由居委会担任监护人、不愿余某鸿担任”的明确表达,应当依法予以充分尊重。这一判断,体现了成年监护制度中对被监护人人格尊严和主体地位的高度重视。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并不等同于意愿被完全排除。
五、监护能力与品行的实质审查
在对余某鸿是否适合担任监护人的判断中,人民法院并未停留在血缘关系层面,而是重点审查其过往行为记录。经查,余某鸿存在隐瞒、私自支取父母财产的情形,对款项用途无法作出合理说明,且长期存在信用卡透支、以父母住房设定抵押等行为。
上述事实表明,其在财产管理能力、诚信程度及风险控制方面存在明显缺陷,不具备妥善履行监护职责的现实条件。
监护制度的核心,不是“谁有资格”,而是“谁更安全”。
六、基层自治组织担任监护人的制度功能
在排除近亲属担任监护人的可行性后,人民法院进一步审查某社区居民委员会的监护适格性。裁判指出,居民委员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具备一定的组织稳定性、公益属性和社会监督基础,在被监护人无适格近亲属的情况下,依法可以承担监护职责。
在本案中,居委会明确表示愿意履行监护责任,且其介入有利于防止被监护人财产被侵害,更符合长期生活照料与权益保障的需要。
社会组织监护,是成年监护制度的重要补充机制。
七、“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的综合适用
人民法院最终指出,在指定监护人时,应当综合考量被监护人的生活稳定性、财产安全、心理安宁及意愿尊重等多重因素,而非单一标准作出判断。
结合余某甫明确意愿、余某鸿存在不利履职情形以及居委会具备履职条件等因素,法院认定由某社区居民委员会单独担任监护人,更符合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
该原则并非抽象口号,而是贯穿证据审查与价值判断的核心准绳。
八、裁判规则的体系化提炼
通过本案,可以提炼出以下具有明确指引意义的裁判规则:
在指定成年人监护人时,应当坚持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
被监护人具备一定认知能力的,其真实意愿应当被充分尊重
近亲属存在不利于履行监护职责情形的,可以不予指定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依法直接担任监护人
监护人指定应当以风险防控和权益保护为核心目标
九、对成年监护纠纷与律师实务的启示
从律师实务角度看,本案提示,在代理成年监护案件时,应重点围绕监护能力、财产风险、被监护人意愿等实质要素展开证据组织,而不宜仅强调法定顺位或亲属关系。
同时,对于基层组织担任监护人的案件,应充分论证其履职可行性与稳定性,以增强裁判方案的现实可执行性。
成年监护案件,本质上是对“安全感”的司法确认。
结语
余某鸿、某社区居民委员会申请指定监护人案,通过对“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的实质化适用,清晰展现了人民法院在成年监护领域从形式规则向实质保护转型的裁判思路。该案不仅为类似纠纷提供了可复制的判断路径,也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成年监护制度的司法实践图景。